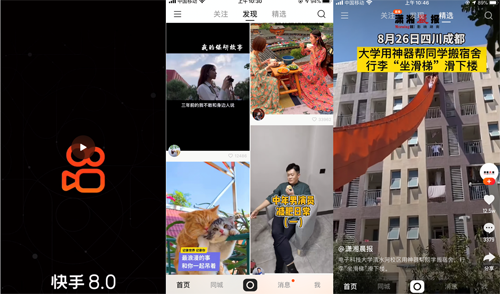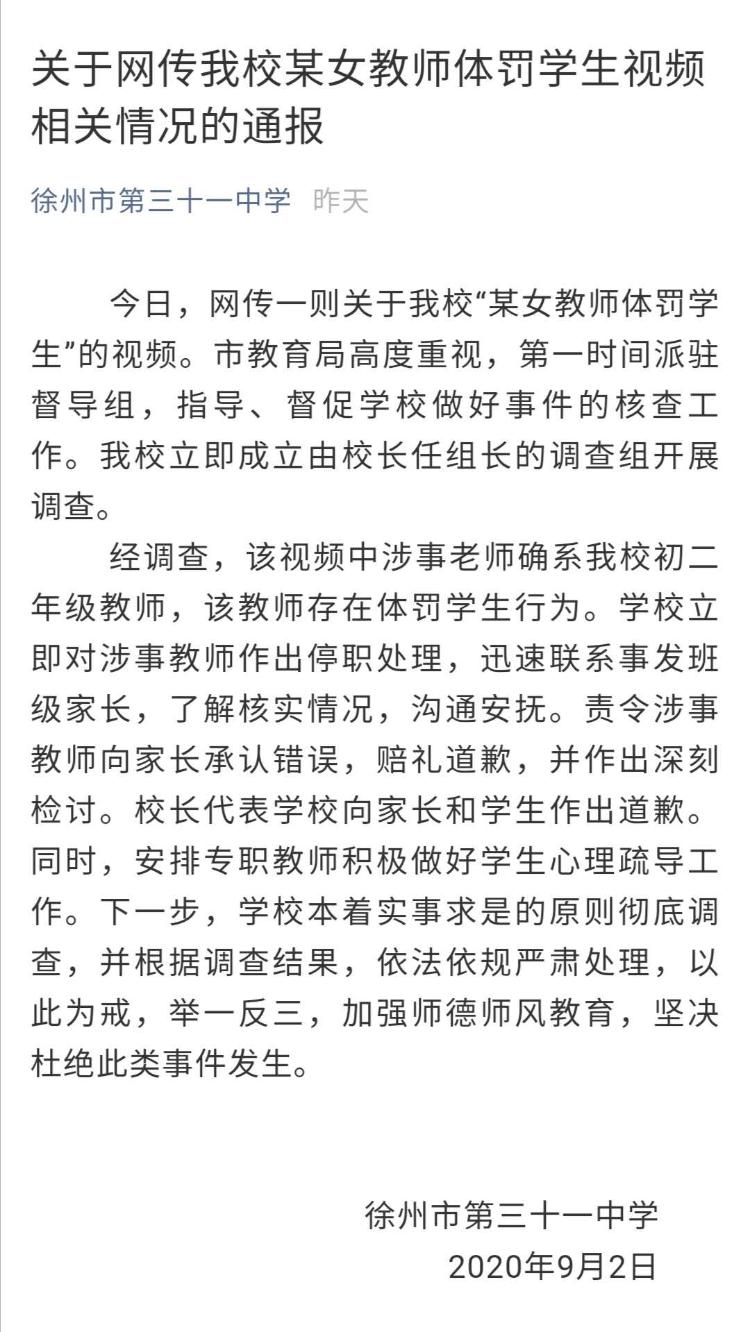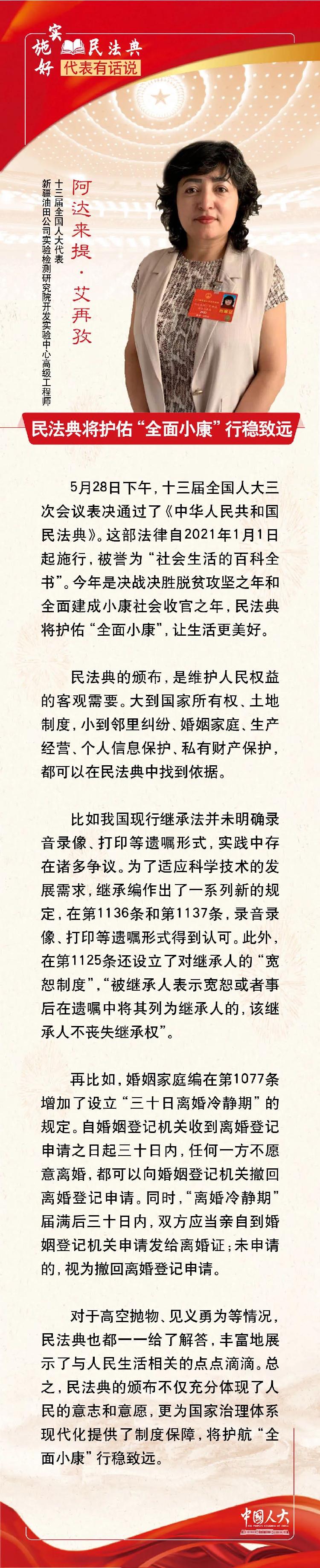不久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一篇新作《弃猫,提起父亲时我要讲述的往事》中,首次向外界公开了一个隐私:其父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并可能在中国战场参与杀害过战俘。在小学时突然听父亲讲到这些后,他对父亲产生疏远与隔阂,一想到“用军刀砍下人头的残忍光景”,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这种“身为侵略者后裔”的羞耻感纠缠着他,自感血液里流淌着历史的原罪,他甚至不想要孩子,以免下一代重复这一痛苦。在成年之后,他一度长达20多年断绝了父子联系,直至父亲在90岁高龄去世前夕,两代人才稍稍和解。
父辈的罪孽是最沉重的遗产,身为后人如何面对它,始终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虽说现代社会大抵都承认,每个人都是与父母完全不同的个体,无须为父辈所犯下的罪恶承担责任,但历史记忆所带来的精神折磨却不会那么容易消退;在这一点上,现代人和生活在传统时代的人们没什么两样:死去的亡灵仍然在不断影响着乃至搅扰着活人。
毫无疑问,这一点对战后德国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纳粹时代的暴政已被普遍视为现代史上(甚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孽。对那些“纳粹的孩子们”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不一般了:除了希特勒没有生育、戈培尔在自杀前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之外,大部分纳粹首脑的子女都活了下来,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去纳粹化的世界里,面对自己父辈的所作所为。
这当然非常难,正如《纳粹的孩子们》一书在开头就说到的:“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说到底,父母不但给了我们血与肉,还深深影响到了我们的想法与行为,他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因而在本质上,评判父母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
不必奇怪,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希姆莱的独女、“纳粹公主”歌德伦·希姆莱坚称父亲是无辜的,认为他并未犯下那些受世人指责的罪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政治人物;戈林的独女艾妲·戈林眼里的父亲也是“棒得不得了”,他完全是爱情、善良和利他主义的化身。她们都认为,唯一应当为纳粹罪行负责的是希特勒,自己的父亲只不过是服从上级罢了。希特勒副手赫斯的儿子沃尔夫·吕迪格走得更远,他甚至否认大屠杀,认为父亲是一个受害者,而非罪犯。希特勒最宠信的建筑师施佩尔的儿子小施佩尔虽然也是建筑设计师,但一生都在不顾一切地跟父亲划清界限,不愿受到他任何影响。德占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五个孩子分裂成三种不同立场:三个子女拒绝接受历史真相;幼子尼克拉斯在得知真相后,对父亲充满恨意,并公开激烈批判德意志民族;长子诺曼则常说“我父亲是个纳粹罪犯,但我爱他”,然而他也和许多纳粹后代一样,拒绝生育,以免将自己家罪恶的基因传下去。
对他们来说,内心交战最甚的是如何面对父辈身上的两面性。很多纳粹要人不论做了什么,在家里都是一个好父亲。战后被指控要为数十万犹太人遭大屠杀负责的艾希曼,曾在受审前对他进行检查的精神科医生指出,他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正是因此,集中营“死亡天使”门格勒的儿子罗尔夫一直纠结在两种情绪中:身为人子,他对父亲有敬爱之情;但一想到他犯下的可怕罪行,又不可遏制地唾弃他。集中营医生维特尔的子女反复讨论下来,还是觉得无法谴责父亲,但让女儿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好人能做坏事吗?”
答案是:能。正如《纳粹医生》一书所揭示的,这些普通人可以在一套心理转换机制之下,在不同场景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完全可能既是一个家庭里的好父亲,又是一个集中营里残忍的魔鬼。希姆莱小时候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对家人也一直很好,但主持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却正是他。很多子女的痛苦,正是来自这种双重性:“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怎么可能成为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汉斯·弗兰克的长子诺曼的话就很典型,他在看到父亲生前的文字时,感到羞耻而困惑:“那不可能是我敬爱的父亲。他身上竟然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无法理解。他的学识那么渊博,对我又那么好,怎么可能会说出那么愚蠢而且充满仇恨的话?”然而,这确实可能,也是在审视父辈时必须要学习的一课,正如马丁·鲍曼的儿子所特别强调的,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学会如何分辨“我父亲的个人身份和他的政治人物兼纳粹官员身份”。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纳粹的后代也是受害者,毕竟那些罪行并不是他们犯下的,但他们却可能因为自己的姓氏而饱受社会排斥。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尔-昂在30多年前就已指出这一点,认为刽子手的孩子在内心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罪恶。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成年,对父亲的公务所知甚少,像希姆莱的女儿歌德伦,在父亲生前总共只见过他不到20次,几乎所有人都是直到战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自己的父辈在第三帝国扮演的角色。客观地说,这也是很多人为父辈辩护的重要原因,因为他们有机会亲自感受到的只是父辈多重人格中“好父亲”的那一面,因而更倾向于否认媒体、书本上揭示的另一些可怕的面向。
但无论如何,罪孽的痛苦不能靠刻意的遗忘与否认来克服。要知道,纳粹的要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也曾是青少年,如果他们对德意志帝国和战败的记忆有所反思,可能就不会出现第三帝国。往事的幽灵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承认并正视它的存在是克服它的第一步。或许也是因此,希特勒的事务总管马丁·鲍曼之子为了消除这一痛苦,最终转向父亲最痛恨的天主教会,成了一名神甫,因为只有在上帝面前,他的内心才能得到平静与救赎。汉斯·弗兰克的长子诺曼常说:“我父亲是个纳粹罪犯,但我爱他。”不过,他也觉得父亲被判死刑好过无期徒刑,因为后者相当于“全家一起坐牢”。在他的墓志铭上刻着一行字:“现在你已从你因为爱父亲而受的痛苦中解脱。”
这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几个纳粹子女的问题,事实上,它事关整个国家。在2014年的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中,首席检察官讥讽试图不懈追查战时真相的主角约翰·瑞德曼:“你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了吗?你想让德国年轻的一代人都问自己的父亲是不是杀人凶手吗?”瑞德曼坚定地回答:“是的,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要这些谎言和沉默全部终结。”然而,他慢慢发现,自己父亲也曾是纳粹,他为此做了一个噩梦:梦中他追查的门格勒转过身来,竟然变成了自己父亲的脸。他未来的岳父酗酒,曾在波兰驻扎过,而这背后也有隐情:“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酗酒?”最后,甚至连一直激励他去追踪这些罪行的同伴,竟然也曾在集中营担任过看守。
战后初期的德国为此选择了避而不谈,希望这段不光彩的历史默默翻篇。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很多年里都没有被列入德国学校教纲,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重建民主的前提是避谈过去。”直到1968年,席卷全球的青年造反派运动,才带来了爆发与觉醒,所谓“68年代人”开始尖锐地追问父辈的过去,引发一场伦理变革:因为如果不清除这些从未被真正打倒的纳粹父辈,改变对他们的依附地位,个人就无法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更早前德国青年运动的回声:年轻人只有反思父辈的作为,激进地反抗和批判父辈,才能“创造空间和自由来抵制来自长辈的阻力”。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日本战后之所以对战争的反思不如德国深刻,原因之一就在于1960年代日本年轻人的反叛很快归于失败而未能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与亲历者的记忆不同,隔代的记忆是一种“后记忆”(post-memory);由于缺乏共同的经历或经验,它是无法直接传承的,而需要不间断的讲述。即便如此,这样的记忆分享也常常是零碎的,需要人们通过影像资料、访谈、重寻故地等方式一起参与,才能使那段历史更生动地呈现出来。吊诡的是:只有正视它才能让整个民族放下重负,但放下重负却又可能使后代不再正视历史而重蹈覆辙。德国自1990年以来就已出现这样的苗头:由于新生代对二战已几乎没有切身记忆,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层面的自责心理,许多人感到终于不再需要背负政治与道德责任,一些年轻人因为无知或无感,对历史不屑一顾,这为“新纳粹”光头党的崛起准备好了社会土壤。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德国问题”,事实上,在那段幽暗的历史上,情形如此复杂难辨,很难有哪一方能宣称自己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波兰一度被视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主要受害者,但前些年爆出的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事件却表明,战时的波兰人主动参与了对犹太邻居的杀戮。不仅如此,根据安娜·比康特《罪行与沉默》一书的深度调查,波兰社会存在着许多抵制反省的声音,因为他们自视为受害者,更何况真相会威胁到太多人的利益与认同。相比起来,不得不说德国社会的反省要彻底得多,也正是这样,德国才赢得了世人的尊敬。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先从正视历史记忆开始。

《纳粹的孩子们》
[法]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