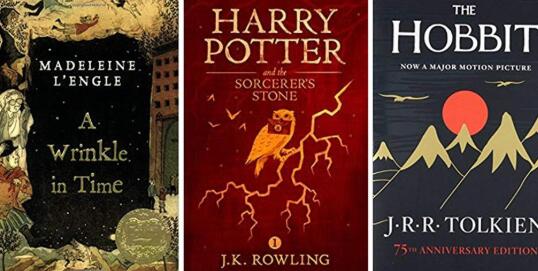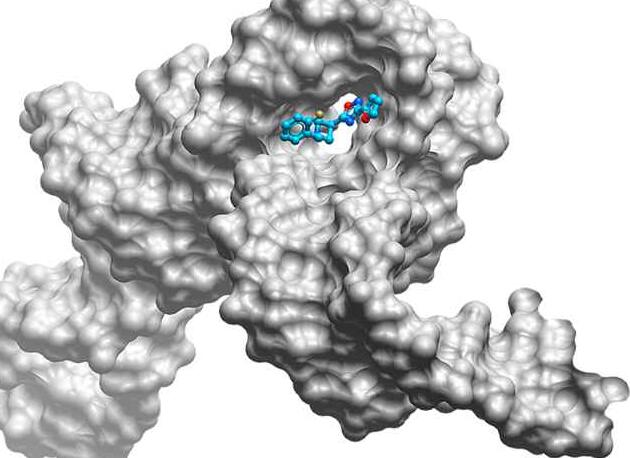自从行为经济学的两位鼻祖丹尼埃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在过去十年之中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这门学科不仅找到了合法性与关注度,甚至展现出了向来执迷于虚无缥缈之供需关系的传统微观经济学最不能企及的优点——实用性。行为经济学家们用他们最擅长的理论工具——市场调研——告诉我们,大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运行方式存在很深的误解。事实上,社会经济行为当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性,甚至连相对理性也是种妄想。并非所有消费者去超市买菜都会严格比价,很多人居然根据颜色买东西,更有甚者(比如我)在双11当天下了5个200块左右的单。行为经济学不相信理性。行为经济学不能告诉企业应该怎么搞宏观投资,但可以告诉商家有百分之多少的消费者看到满减就有凑单的本能,又有百分之多少看到领红包三个字就头脑发热,可以为了领一块钱戳一整天的手机。每个愚蠢的人类都是不可错过的商机,反过来,每个商机背后都是一排排愚蠢的人类——我们的社会经济是围绕愚蠢而非智慧运行的。
英国人鲍比·达菲(Bobby Duffy)的新作,把这套“人类蠢不可耐”理论又往前推了一步,他的处女作书名叫《为什么我们几乎全错:人类误解理论》(Why Were Wrong about Nearly Everything:A Theory of Human Misunderstanding)。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英国出版时还有另一个名字——《感知的危险》(PerilsofPerception),这么个绕口令一样“精英主义”的标题,很快被深谙人类文化水平的美国出版商给删了。跟卡尼曼和塞勒的经济学背景不一样,达菲的背景是市场与民意调研,他在著名国际调研公司IpsosMori干了20年,而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数据与结论都来自Ipsos在全球各国所做的调研。
读此书前,有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我们最好不要去想,比如为什么搞市场调研的人明知道参加所谓“焦点小组”的人全都是拿了钱的托,却总认为自己得到的数据真实可靠;或者说,如果搞市场调研的人问一个小组“你幸福吗”的时候,难道不知道任何真的幸福的人不会为了几百块钱参加焦点小组吗?又比如,在我们读到书名里的“我们”时,我们不得不想,我们是不是这想什么都错的“我们”里的一部分,而不管是不是,我们岂不都又错了一回?
你如果像我一样想这些问题,便成了达菲称为“情感数盲”(emotional innumeracy)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很喜欢用一些由两个词组成的术语,类似的还有“认知偏差”或者“理性无知”之类。什么是“情感数盲”?其实就是一些会根据自己的感情、偏见或无知对问卷调查中涉及数字的问题做出非常离谱的猜测的人。比如出于我本人对市场调研这种研究方法的不信任态度,我做出了一种不负责任、完全感情用事的猜测,认为所有(100%)参加市场调研的人都不幸福,但这显然与市场调查得来的结果相去甚远——事实上,根据达菲书中Ipsos的调研,中国有85%的人自称幸福或者还算幸福。
再举一个更好理解的例子,达菲的调研让来自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45~54岁男性和女性猜测这个年龄段的人一生中性伴侣的数量,并同时给出自己性伴侣的数量。结果是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性伴侣数量的猜测基本符合男性自己提供的答案,而男性对女性,以及女性对女性的猜测却不着边际。美国男性认为美国女性平均有27个伴侣,甚至有填写50个或更多的,英国女性猜测英国女性平均有18个伴侣,而英国女性的答案只有8个。更荒唐的是,三国男性自己报告的性伴侣数量平均在17个左右,三国女性自己报告的性伴侣数量平均下来却只有10个。这在数学上是不成立的(除非男性在54岁以后平均交往7个以上性伴侣),因此,从统计意义上说,参与此次调研的人平均都在撒谎,不是男人多报就是女人少报。
我不知道达菲和Ipsos有没有做过结果是人类猜得挺准的调研,因为他在书中举出的例子全部是偏差严重的情况。另一个调研,问参与者“你认为自己国家20岁以上的人当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有糖尿病”。根本没有一个国家的人猜得靠谱。最准的是挪威人,回答17%,实际数据是6%。大部分国家参与调研的人,竟然给出平均值超过40%的答案,而糖尿病百分比最高的国家(沙特阿拉伯)也只有20%。同样令人尴尬的情况涉及每个领域,比如被问到自己国家有多少移民的时候,中国人回答11%(实际不足0.1%),美国人回答33%(实际为14%),英国人回答25%(实际为12%),括号内均为官方数据。不仅如此,在移民这个目前主导西方政治的问题上,当参与调研的人员被告知自己错得离谱的时候,依然不依不饶,47%的人认为官方数据不含非法移民,45%的人就是认为自己猜得没错,37%的人认为自己的答案符合平时的观察,还有11%的人说自己填写的数字是从电视或正规媒体上看来的。
人类的愚蠢与谬误到这里竟还没结束,达菲举出了更多卡尼曼和塞勒过去用过的例子,比如塞勒著名的“当下偏见”和“双曲贴现”理论——让一个人选吃水果还是巧克力的时候,如果是未来时态,大部分会选水果,但如果是此时此刻,大部分人会选巧克力;或者如果我们对这不指名的巧克力和水果哪个更好吃不能百分百确定的话,例子可以换成现在给你10块钱,还是明天给你12块,大部分人会选择今天拿10块。这构成了行为经济学中对政府与企业决策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也就是做任何预算的时候如果根据纯粹的理性分析,那么最后肯定是要被人类的愚蠢打败的。达菲在这个领域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的调研显示,10个英国人里有3个认为如果退休后每年需要2.5万英镑生活费的话,自己退休前只需要存5万英镑就够了。哪怕平均数也认为只需要存12.5万英镑。事实上根据目前的推算,净资产必须达到35万美元以上,才能靠吃利息和领政府养老金凑满生活费。而很显然,根据“水果巧克力原则”,如果你让人们选择是今天把所有养老金一笔全拿出来,还是一直吃利息,很大一部分人会选择前者。
行为经济学的本体论,是它只承认一个主体——平均主体(这个双词术语为本人发明)。在此前提下,至少从达菲的调研来看,很显然,这个最能代表我们全人类的只在统计学意义上存在的平均主体智商很成问题。它无法分辨事实和想象,真新闻与假新闻;它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仅感情用事还很固执;它对国家大事存在很多相当离谱的误解且不接受反驳;它急功近利,做不到未雨绸缪,且惰性很强,经常因为懒而损失各种利益——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这个想什么都错的平均主体究竟是什么模样?
有一个人影渐渐浮现——唐纳德·特朗普。
在达菲对特朗普和所谓“后事实”时代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滑稽的现象——满嘴跑火车的特朗普表达过的很多观点,与达菲做的民调当中得来的答案出奇地一致。比如他的选择性“情感数盲”——达菲举例:2017年特朗普曾在白宫会议上说,当年美国谋杀率创下47年来的新高,而真实数据是2015~2016年之间美国城市中谋杀案的上升率是45年来最高;他经常传播虚假新闻,又骂不支持他的媒体报的全是假新闻;他会不由自主夸大自己的能力;诸如此类。根据达菲的理论,特朗普正是那个“想什么都错”的平均主体——一个实实在在的“智商中位数”。
有些人如耶稣想当救世主,有些人如尼采想当超人,而另有一种人愿意花几百万雇用百十个行为学家把自己变成“平均主体”——那种人就是民主社会的政客。希拉里·克林顿用AI都做不到的事,特朗普什么也没干就做到了。过去三年来,很多人提供了更多特朗普为何能当选的理论,在我看来,没有比达菲无心插柳的解释更确切的了——也许特朗普正是愚蠢人类的终极化身?作为愚蠢的人类,有什么理由不选自己的化身来领导自己?
达菲当然并不这样理解问题。过去几十年,从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发家的技术官僚或技术学院派,有个同样无药可救的通病,就是他们能把数据变戏法一般变成能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框架的东西。承认人类愚蠢对技术官僚与技术学院派则不是选择,只有“如何打倒认知偏差”才是可获研究资助的议题——像那些商学院励志心灵鸡汤一样,听起来好像很可行,但在“怎么打倒”这个问题上,达菲像所有人一样无计可施。达菲在书的末尾竟然列出了十条建议,如“要怀疑但不要犬儒”,或者“其他人跟我们没那么像”,或者更鸡汤的——“一切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且正变得更好”。至于什么是“好”,技术官僚通常默认为他们脑中的乌托邦愿景,如男女平等、环境改善、消灭贫困之类。
达菲书中有个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很荒诞,但能以极高的精炼度代表技术官僚总体思维模式的案例——在瑞典某个城市,冬天的扫雪工作被认为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因为铲雪通常从市中心商业区开始,最后才铲到城市边缘的小路上。这一直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思想先进”的技术官僚们意识到在市中心商业区上班的大多是男性,而在城郊生活的很多是女性,另外,调研显示女性开车的比男性少,而更多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因此在这座瑞典城市的冬天,女性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高于男性。由于传统官僚男性居多,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于这座瑞典城市。技术官僚们在意识到这点后,决定从小路和人行道开始铲雪,先铲通往托儿所的路,接着开始铲市中心的雪,并把女性员工较多的工作场所(医院、学校等)包括在第二等级的铲雪路线里,最后再铲其他道路。根据这份达菲引用的报告,铲雪费用没有增加,事故率与受伤率却大幅降低——这里,像我这样的犬儒主义者通常要不合时宜提出自己十分消极的问题——如此作业,在市中心工作的员工(男女不限)还能不能按时上班?通勤时间是否大幅增加?住在市中心的普通人(男女不限)的受伤率是否开始上升?如果我们做一次民意调查,有多少当地人真的支持这一举措?
达菲书末过分积极向上的建议,似乎与前文里对愚蠢人类想啥错啥的描述格格不入,但仔细想想,我们人类的平均主体本来就过分积极也过分虚伪,这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人们被调研问及“你是否幸福”时,回答“幸福”或“比较幸福”的永远在80%以上(匈牙利人除外,这国家的人回答自己幸福的只有69%,且在猜测其他匈牙利人是否幸福时,他们的答案同样垫底,只有22%;韩国人则最虚伪,回答自己幸福的有90%,而猜测他人幸福的只有24%)。因此,很可能,我们的技术官僚同样是我们愚蠢人类理所应得的代表。

《为什么我们几乎全错:人类误解理论》
(Why Were Wrong about Nearly Everything:A Theory of Human Misunderstanding)
[英]鲍比·达菲(BobbyDuffy) 著
BasicBooks 2019年11月版